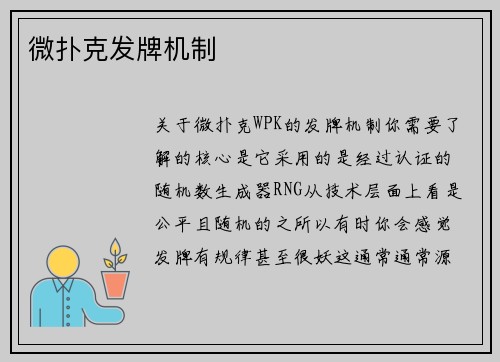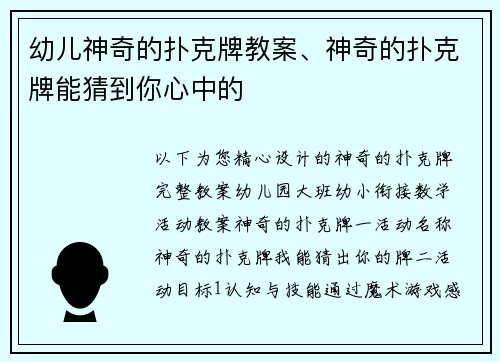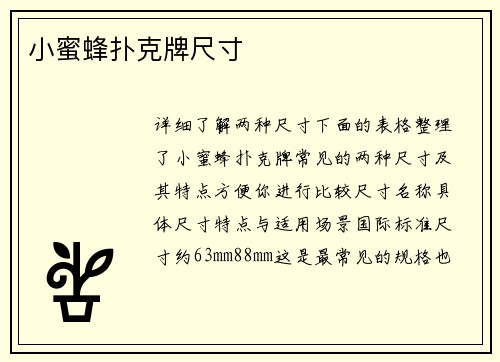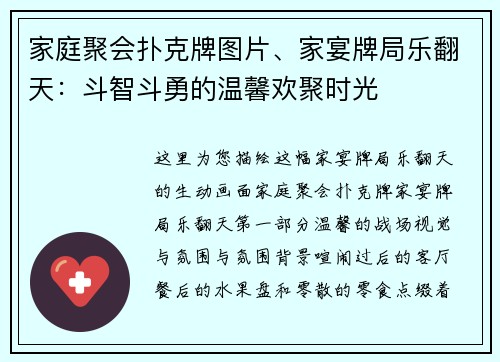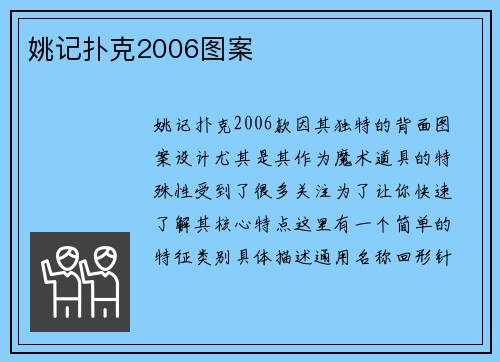>村里人都说我疯了,半夜总在坟地跳舞。
>因为婆婆逢人便哭:“我家媳妇中了邪,天天把毒药当补汤喂我喝。”
>直到那天,她颤抖着撕开我衣袖——
>青紫疤痕下,埋着三十年前被她活埋的陪嫁丫鬟的玉镯。
水汽氤氲,粘稠得糊在口鼻上。文秀端着那碗深褐色的药汁,站在东屋紧闭的房门前,像一尊即将被潮气锈住的雕像。屋里传来断断续续的、压抑着的咳嗽声,一声接一声,掏心掏肺。她深吸了一口带着霉味的空气,推门走了进去。
“妈,药煎好了,您趁热喝。”她的声音不高,平直得像一条拉紧的线,没有任何起伏。
婆婆张桂英靠在床头,浑浊的眼睛在她脸上扫了一圈,随即又耷拉下去,盯着自己枯瘦的手,有气无力地摆着,“放着吧……没胃口,等会儿再喝。”
文秀没动,依旧端着碗,碗沿滚烫,指尖很快被灼出一圈红痕。“王大夫说了,这药得按时喝,凉了药效就过了。”她往前又递了半分。
张桂英猛地抬起头,眼神里闪过一丝极快的光,像是厌恶,又像是某种更深的东西,她死死盯了文秀几秒,嘴角往下撇出一个痛苦的弧度,终究还是颤巍巍伸出手,接过了碗。她的手指碰到文秀的手背,冰凉,像某种冷血动物。
药汁黑得不见底,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苦涩气味。张桂英闭上眼,眉头紧锁,仿佛忍受着巨大的折磨,一小口一小口,极其缓慢地将那碗药喝了下去。每喝一口,她的喉管都发出艰难的吞咽声。
文秀静静地看着,直到碗底空了,才接过空碗,转身出去。自始至终,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,既没有关切,也没有不耐。
第二天,同样的时间,同样的场景。只是这一次,张桂英刚喝完药,捂着胸口干呕了两声,眼泪毫无征兆地落了下来。“秀啊……”她声音哽咽,带着一种被磨尽希望的疲惫,“妈知道……你是好心……可这药……妈喝了心里头发慌啊……”
文秀拿着空碗的手顿了顿,垂着眼睫:“王大夫开的方子,都是温补的。”
张桂英不再说话,只是默默地流眼泪,肩膀耸动着,脆弱得像个孩子。
文秀退出屋子,轻轻带上门。隔着薄薄的门板,她能听到里面压抑的、破碎的呜咽声。她站了一会儿,然后转身去了灶间,把药罐子刷洗得干干净净。
不知从哪天起,关于文秀“疯了”的闲话,就像河边的湿气,悄无声息地渗进了村子的每个角落。
“听说了吗?老张家那个媳妇,半夜不睡觉,跑到后山乱坟岗子上跳舞呢!”
“真的假的?我的天爷!我说桂英婶子最近脸色怎么那么差,原来是……”
wepoker官网“可不是嘛!桂英亲口跟我说的,她那媳妇熬的药,味道不对,喝下去浑身不得劲,指不定往里加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!”
“中邪了!肯定是撞客(撞邪)了!好好的一个人,怎么就……”
这些话,自然有几句半句,被风刮进文秀的耳朵里。她依旧每天沉默地操持家务,下地干活,给婆婆煎药,送药。只是偶尔,在河边捶打衣服时,或者在田埂上歇脚的片刻,她会抬起眼,望着远处雾气缭绕的山峦,眼神空茫,不知道在看什么。
她的沉默,在村民们看来,坐实了“疯病”。她的不合群,成了“鬼上身”的证据。人们看她的眼神,渐渐从最初的同情、疑惑,变成了畏惧和避之不及。
一天下午,文秀从地里回来早些,刚走到院门口,就听见里面有几个老太太的声音,其中以张桂英的哭诉最为清晰:“……我是造了什么孽啊!娶了个这样的丧门星回来……那药苦得钻心,喝下去我这心口就跟刀绞似的……她说那是补药,谁家的补药是这样的?我瞧着她眼神都不对了……晚上总往外跑,拦都拦不住……我这把老骨头,怕是迟早要死在她手里头……”
文秀的脚步停在原地,没有进去,也没有离开。她听着婆婆那熟悉无比的、带着哭腔的控诉,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,只是搭在院门上的手,指节微微泛了白。
日子就这么在诡异的诡异的平静与暗涌的流言中滑过。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,浓墨般的夜色裹挟着蛙鸣。文秀悄无声息地下了床,穿上那件半旧的蓝布衫子,动作轻缓地拉开房门,融入了夜色里。
早就留心着她的几个胆大的村民,互相使了个眼色,蹑手蹑脚地跟了上去。
她果然往后山去了。
夜里的乱坟岗,荒草没过膝盖,夜枭偶尔发出一两声凄厉的啼叫。磷火幽幽地飘荡,像找不到家的孤魂。文秀的身影在荒冢残碑之间,显得格外单薄。她停在一片稍微平整的空地上,然后,真的开始动了。
不是跳舞。
她的手臂缓缓抬起,落下,身体以一种奇异的、僵硬的韵律摆动,更像是某种古老的、笨拙的仪式,或者说,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挣扎。她的长发披散下来,随着动作晃动,嘴里念念有词,声音很低,被风吹散,听不真切。
躲在远处树后偷看的偷看的几个人,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窜上天灵盖。这不是跳舞,这分明就是……鬼附身!
他们连滚带爬地跑回了村子。
“疯了!真的疯了!”
“在坟头跳大神啊!吓死个人!”
张桂英听到这个消息时,正坐在自家堂屋的椅子上。她先是露出惊恐万状的神色,随即拍着大腿嚎啕起来,哭自己命苦,哭儿子死得早,哭家门不幸。来“报信”和围观的人挤了一院子,议论纷纷,看着文秀的眼神充满了赤裸裸的恐惧和排斥。文秀已经被先回来的人堵在了院子里,她站在那里,不说话,也不辩解,像狂风暴雨中一棵沉默的树。
混乱中,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:“捆起来!送到镇上去!请先生来看看!”
人群骚动起来,有人找来了绳子。张桂英哭得更凶了,扑过来似乎想护住文秀,却被旁人拉住。“让我死了算了!我没脸活了呀!”
就在推推搡搡,一片闹哄哄的时候,张桂英脚下不知被什么绊了一下,一个趔趄向前扑去,慌乱中她伸手想抓住什么保持平衡,一把攥住了文秀左边胳膊的衣袖。
“刺啦——”
那件半旧的蓝布衫袖子,从肘部到手腕,被整个撕裂开来。
所有的声音,哭嚎、议论、叫嚷,在这一瞬间戛然而止。
院子里屋檐下挂着的灯泡,光线昏黄,但足以让足以让所有人都看清——
文秀那只裸露出来的小臂,从手腕上方一点开始,密密麻麻,布满了新旧交叠的伤痕。有已经发暗发紫的陈旧淤痕,有颜色较深的棍印,还有几道结了痂又被蹭破的血痕,狰狞地盘踞在她苍白瘦削的胳膊上,一直延伸向袖筒更深处。
而在那片不堪入目的皮肉之上,接近手肘的地方,赫然套着一只玉镯。
那玉镯质地算不上顶好,颜色是淡淡的豆青色,样式也老旧。但奇异的是,它仿佛是从皮肉里长出来的一般,紧紧地嵌在肉里,镯子边缘的皮肤因为常年摩擦和挤压,呈现出一种不正常的红肿和增厚,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玉质与皮肉粘连在一起的、略微发亮的疤痕组织。
那不是戴上去的,那更像是……被什么东西硬生生烙进去的,或者,是皮肉在某种外力下,包裹着它长合了。
死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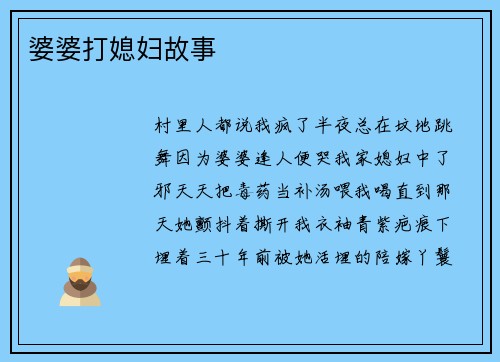
张桂英的哭声停了,眼睛瞪得几乎要裂开,死死地盯着那只玉镯,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,嘴唇不受控制地哆嗦起来,喉咙里发出“咯咯”的、像是被扼住脖子的声音。
她认得这只镯子。
三十年前,那个跟她一起嫁到张家的、水灵灵的陪嫁丫鬟小桃,手腕上就戴着这么一只镯子。是她,张桂英,因为嫉妒丈夫多看了小桃两眼,在一个雷雨夜,诬陷小桃偷了她的金簪,命人用家法往死里打。小桃断气前,那双充满怨恨的眼睛,就一直盯着她。后来……后来是她亲自看着人,把还有一口气的小桃,连同一些“不吉利”的东西,一起拖到后山,草草埋了的。
埋的时候,小桃手腕上,就戴着这只豆青色的玉镯。
它怎么会…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?长在了文秀的胳膊上?
张桂英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,又像是看到了世间最恐怖的景象,浑身筛糠般抖起来,手指颤抖地指着那只玉镯,想要尖叫,却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,只有嗬嗬的倒气声。
文秀慢慢地,把自己的手臂从婆婆那冰冷僵硬的手指间抽了回来。她低头,看着自己布满伤痕的手臂和那只诡异的、嵌在内里的玉镯,然后,抬起眼,目光平静地落在面无人色、抖如秋叶的张桂英脸上。
她忽然很轻很轻地笑了一下。
那笑容里,没有疯癫,没有怨恨,甚至没有任何温度,只有一片沉静如水的、令人骨髓发寒的了然。
她什么也没说。
但那无声的笑容,比任何凄厉的指控都更锋利,直直刺入张桂英的魂魄深处。